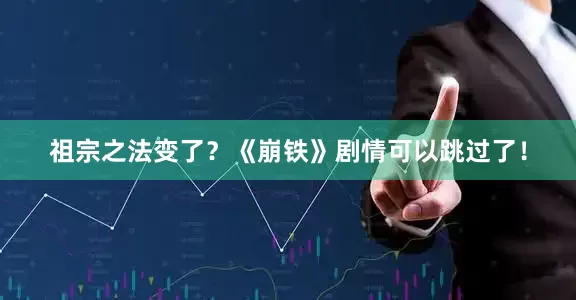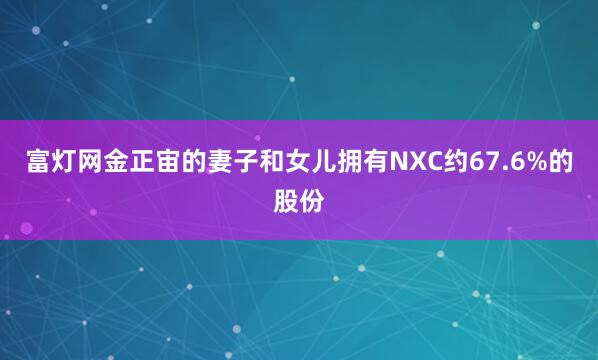唐武宗的“会昌中兴”具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志——“会昌伐叛”。这次运动不仅消除了刘氏父子所建立的割据势力,还成功地收回了对昭义镇的控制权。昭义镇囊括泽、潞、邢、洺、磁五个州,它位于河北和山西的交界地带,扼守着关中与关东的门户,是兵家必争之地。长期以来,昭义镇在平定河朔之乱中扮演了桥头堡的角色,战略地位可见一斑。
昭义军的历任节度使一直由朝廷任命,并且忠心耿耿。然而,历史的转折往往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——他就是刘悟。最初,刘悟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手下的一名兵马使,在平定淄青叛乱时,他背叛了李师道,亲手斩杀了李师道父子,迅速由叛臣转变为朝廷的功臣。在常规情况下,刘悟应该接管淄青,但唐宪宗却使了一招巧妙的调兵之计,将刘悟调任了义成节度使。义成的地理位置狭小,管理难度较大,刘悟本应愤而反叛,但唐宪宗以铁腕手段铲除了其他割据势力,刘悟此时并未反抗,而是选择保持低调。
展开剩余78%不幸的是,唐穆宗继位后,操作不当使得已经平定的河朔三镇再度反叛。出于对刘悟可能参与叛乱的担忧,穆宗将其调任昭义节度使,试图将其置于三镇的影响之外。表面看,唐穆宗的这一步棋似乎是聪明的,但却为昭义镇的割据埋下了隐患。刘悟上任后,与监军刘承偕发生了激烈冲突,监军历来自诩为皇帝的亲信,但刘悟显然并不买账,两人矛盾愈加加深,最终刘承偕被迫逃回长安。唐穆宗一方面不满刘悟的悖逆,一方面又无力纠正,最终只能选择放任。刘悟反而因此变得更为张狂,他收纳了大量朝廷的失意之徒,逐渐掌控了昭义军。
四年后,刘悟去世。在临终时,他向朝廷提交了一份报告,提出希望儿子刘从谏接任昭义节度使。表面看,刘悟言辞恳切,实则只是走个程序。尽管李绛坚决反对,认为昭义地理位置太重要,不应由刘家继续把持,但李逢吉和王守澄却站在了刘家的立场上,支持刘从谏的接任。最终,刘从谏顺利接手昭义军,成为新的节度使。
刘从谏继任后,依托着昭义军的庞大财力,经营了多个垄断行业,包括马匹、盐、铜铁等。依靠这些资源,他获得了巨大的财富,并通过贿赂朝廷官员,迅速与朝中红人建立了深厚关系。然而,这也使他与宰相李逢吉等人的对立日渐加剧。随着李训等人被诛杀,刘从谏与仇士良的矛盾更加公开化。他甚至送给唐武宗一匹宝马,却遭到了拒绝,愤怒之下,他将宝马杀掉,彻底破裂了与朝廷的关系。
事态逐渐逼近顶点。刘从谏患病临终时,心中极度担忧自己家族的命运。于是他将节度使的职务传给了侄子刘稹。然而,刘稹上任后立即采取了自立的举动,拒绝接见朝廷使者,甚至在使者面前展现了武力,威胁要继承节度使的职位。这一举动激怒了朝廷,唐武宗震怒,下令进行讨伐。然而,由于多重原因,讨伐进展缓慢,李德裕不得不亲自介入调度。
李德裕作为朝廷的铁血宰相,迅速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,派兵围攻昭义镇,先后攻破了刘稹的多个堡垒,并最终促使刘稹的叛乱走向终结。在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后,刘稹被亲信刺杀,昭义军重新回到朝廷的掌控中,刘家最终也灭族。
那么,中唐以后,为什么藩镇割据局面愈演愈烈呢?刘家的割据,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?我认为,藩镇与中央的利益冲突是根本原因。藩镇节度使拥有过大的财权、军权和人事权,成为了一个“地方小朝廷”,这本质上破坏了中央集权的稳定。刘从谏虽然表面上为朝廷效忠,但实际上,他的行为已经走向了自立门户的道路,而朝廷对他的容忍,也促使了割据的加剧。
此外,宦官的崛起也打破了原本的二元权力结构。宦官掌握了皇帝的信任,成为了朝廷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。在士族和藩镇失去皇帝信任后,宦官的权力逐渐膨胀,使得许多藩镇节度使无法安心待在自己的位子上,最终选择了割据一方。
最重要的是,庶族阶级与军权的结合使得像刘家这样的家庭有了自立门户的可能。在唐朝,庶族虽然没有太多机会进入中央,但地方的军权给了他们反抗豪门的机会。当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,割据局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,而这正是导致大唐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发布于:天津市盛达优配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